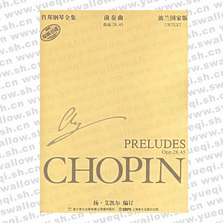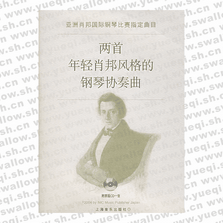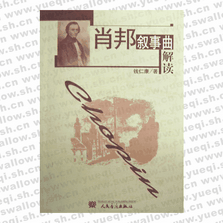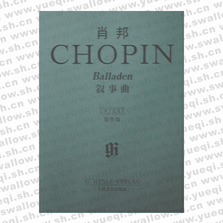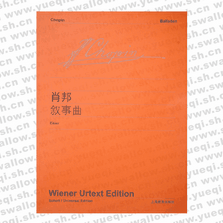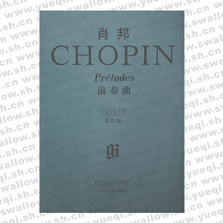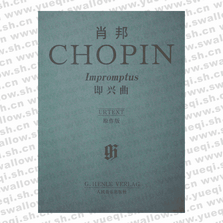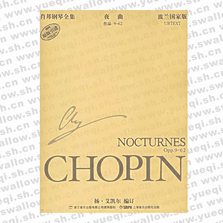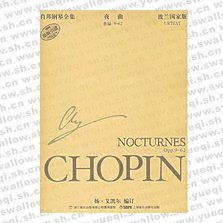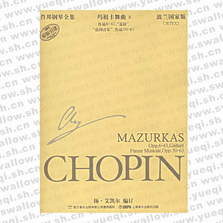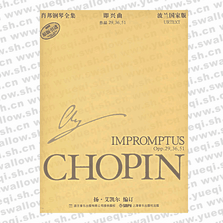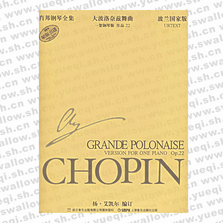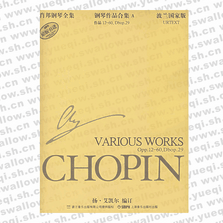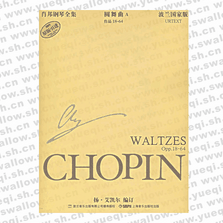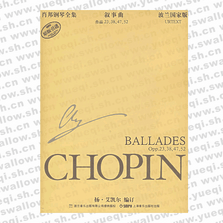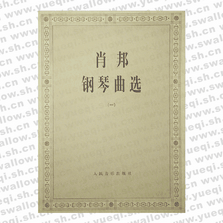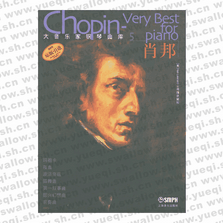艾凱爾教授曾在1983年訪問中國,并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作有關肖邦的專題講座。現在由他編訂的波蘭國家版《肖邦鋼琴全集》在中國出版,使他對肖邦的研究成果受到更廣泛和全面的傳播,相信必將又一次引起音樂界的重視。
肖邦的作品是所有鋼琴文獻中被演奏得最多,但也被篡改得最嚴重的。六十年前,我們不懂什么是“原始版”(Urtext),那時也沒有“原始版”,以為只要是肖邦,什么版本都是一樣的。后來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,各種版本之間差異很大,有的是編訂者有意修改,以為可以“改進”肖邦的原作(如Karl Klindworth版[1830-1916]),大多數是以訛傳訛,以為本應如此。上世紀中,波蘭出版了帕德雷夫斯基(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-1941)版,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以前的謬誤,并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肖邦演奏風格。這個版本在國際上流行了整整半個世紀以上,但是它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“原始版”,它用所謂“標準化”的辦法,把肖邦手稿中許多細微的變化“標準化”(簡單化)了。
艾凱爾教授是當今最權威的肖邦專家,他本人是鋼琴家、教授,有幾十年的演奏和教學經驗,又是一位學識淵博、治學嚴謹的學者,由他主持編訂一部新的肖邦“原始版”當然是再合適不過的。這部新的“原始版”被波蘭政府定為“國家版”,以示其重要性和權威性。艾凱爾教授不但根據肖邦的手稿、各種初版,而且掌握了肖邦教學時在學生用譜上的許多修改和更正,因此他這個版本中有許多新的發現,和我們習慣聽到的大異其趣。相信這將成為又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肖邦的作品是所有鋼琴文獻中被演奏得最多,但也被篡改得最嚴重的。六十年前,我們不懂什么是“原始版”(Urtext),那時也沒有“原始版”,以為只要是肖邦,什么版本都是一樣的。后來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,各種版本之間差異很大,有的是編訂者有意修改,以為可以“改進”肖邦的原作(如Karl Klindworth版[1830-1916]),大多數是以訛傳訛,以為本應如此。上世紀中,波蘭出版了帕德雷夫斯基(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-1941)版,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以前的謬誤,并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肖邦演奏風格。這個版本在國際上流行了整整半個世紀以上,但是它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“原始版”,它用所謂“標準化”的辦法,把肖邦手稿中許多細微的變化“標準化”(簡單化)了。
艾凱爾教授是當今最權威的肖邦專家,他本人是鋼琴家、教授,有幾十年的演奏和教學經驗,又是一位學識淵博、治學嚴謹的學者,由他主持編訂一部新的肖邦“原始版”當然是再合適不過的。這部新的“原始版”被波蘭政府定為“國家版”,以示其重要性和權威性。艾凱爾教授不但根據肖邦的手稿、各種初版,而且掌握了肖邦教學時在學生用譜上的許多修改和更正,因此他這個版本中有許多新的發現,和我們習慣聽到的大異其趣。相信這將成為又一個新的里程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