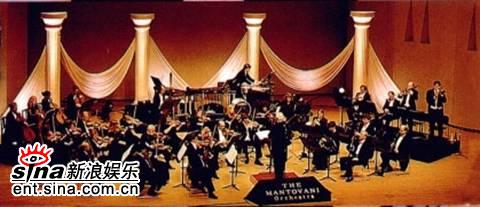每到周末,數(shù)十個(gè)人從四面八方趕來,手持各種民族樂器,在福建閩侯縣三福小區(qū)的空地上演奏。悠揚(yáng)的曲調(diào)總會吸引不少人駐足。
這些演奏者都是閩侯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的成員。團(tuán)員中年齡最大的65歲,最小的不到5歲。目前,樂團(tuán)中經(jīng)常參加活動的有36人,一旦有大型活動,可達(dá)57人。
5年來,他們風(fēng)雨無阻,在千年古邑閩侯,把興趣、愛好與挖掘、保護(hù)、傳承民族音樂結(jié)合在一起,讓民族音樂在鄉(xiāng)間跳動。在第二屆省社區(qū)文化藝術(shù)節(jié)中,他們演奏的余祥云改編的《春韻》,獲得整體節(jié)目第二名、器樂合奏第一名的好成績。
癡迷民樂的余祥云自己學(xué)著做了把京胡。1977年恢復(fù)高考,靠著一手京胡技藝,他考上了福建師范大學(xué)藝術(shù)系。
說到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,先得認(rèn)識一個(gè)人,他叫余祥云,閩侯一中高級教師、省內(nèi)頗有名氣的二胡演奏家。
今年51歲的余老師,是閩侯白沙鎮(zhèn)大目埕村人。祖輩、父輩癡迷閩劇,奶奶曾創(chuàng)辦了村里的閩劇團(tuán)。小學(xué)開始,余祥云就跟隨父親、堂哥學(xué)習(xí)京胡,唱京劇、閩劇。“那時(shí)候,完全出于興趣,他們也沒經(jīng)過正規(guī)訓(xùn)練,主要靠自學(xué)。”
上中學(xué),余祥云擁有了自己的京胡。“打了條老蛇,弄幾塊竹片,就自己學(xué)著做了。”余老師說,當(dāng)時(shí)一把京胡至少要7至8元,相當(dāng)于一個(gè)月的工資,沒有錢,只能自己動手。
高中時(shí)代,余祥云參加了公社組織的文藝宣傳隊(duì),一把京胡讓他感受到了價(jià)值和樂趣。1975年高中畢業(yè)后,余祥云回家務(wù)農(nóng),在那兩年半的日子里,白天勞動,夜晚無論多累,他都要拉上幾段。1977年恢復(fù)高考,余祥云靠著一手京胡技藝,考上了福建師范大學(xué)藝術(shù)系,主攻二胡。
1982年大學(xué)畢業(yè)后,余祥云分配到南平師范。除了教授二胡,他還執(zhí)教鋼琴、音樂理論等,并任音樂教研組長。
2000年,余祥云調(diào)回老家閩侯,任縣一中音樂老師。無論在哪里,處在人生哪個(gè)階段,余祥云始終保持著對民族音樂的癡迷。
2003年,余祥云牽頭成立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。教師、醫(yī)生、機(jī)關(guān)干部、拖拉機(jī)手等各行各業(yè)的人,為著挖掘、保護(hù)和弘揚(yáng)民樂這一共同目標(biāo),走到了一起。
閩侯是閩劇的發(fā)祥地,還曾是十番音樂、評劇、折子戲等民族音樂的沃土。然而,回到故鄉(xiāng)的余祥云卻發(fā)現(xiàn),這里已很少人唱,更少人懂。
嚴(yán)峻的現(xiàn)實(shí),讓余祥云心痛不已。難道就讓民族音樂這樣消亡?作為一個(gè)民族音樂的研究者和愛好者,他覺得應(yīng)該做點(diǎn)什么,讓民樂重新在閩侯“熱鬧”起來。
2003年8月,閩侯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正式成立。8名因?yàn)閻酆米叩揭黄鸬娜耍蕴脱徶昧硕⒁繇憽P(yáng)琴等,在余祥云家20多平方米的雜物間,奏出了美妙的民族之樂。
余祥云對團(tuán)員的音準(zhǔn)、節(jié)奏、手勢、坐勢、工序等逐一進(jìn)行指導(dǎo),并布置“作業(yè)”讓團(tuán)員練習(xí)。團(tuán)員演奏水平很快得到提高。因?yàn)橛辛诉@個(gè)樂團(tuán),有了余祥云的專業(yè)指導(dǎo),這個(gè)團(tuán)吸引力越來越大。愛好民樂的群眾紛紛加入,有教師、醫(yī)生、機(jī)關(guān)干部,也有學(xué)生和拖拉機(jī)手。
今年63歲的吳海光是首批加入樂團(tuán)的成員。他對二胡很感興趣,但是“曲不成調(diào)”。“以前求教無門,只能自己瞎擺弄,水平有限。現(xiàn)在,有了余老師的悉心指導(dǎo),進(jìn)步顯著,我已是業(yè)余六級水平。”
張光巖是閩侯上街的農(nóng)民,平時(shí)靠開拖拉機(jī)運(yùn)貨過活。遇到要白天合練,張光巖定會放下手頭的活,趕到縣城參加,一天幾百元也不賺了。“我們都是‘大學(xué)生’――大了的學(xué)生,以前雖然想學(xué),但沒人教,因此要更加認(rèn)真練習(xí)。”
5年來,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已先后創(chuàng)作、整理、排練了多部鄉(xiāng)土民樂及閩劇、京劇改良曲子。大型民族管弦樂《春韻》、《二泉映月》、《京調(diào)》等已排練成熟。目前,正在緊張排練由傳統(tǒng)閩劇改編的《寶蓮燈》、《曲判記》唱腔片斷和現(xiàn)代京劇《杜鵑山》、《亂云飛》等民樂合奏曲目。“以曇石山為背景的大型民族管弦樂《曇石山隨想》,已創(chuàng)作了兩個(gè)部分,剩余三個(gè)部分正在創(chuàng)作中。”余祥云說,傳統(tǒng)閩劇的缺點(diǎn)是經(jīng)典唱段幾乎沒有,更沒人能唱得清楚。通過改編,如今在排練演出過程中,許多群眾都很驚訝,還有這么好聽的閩劇。
通過藝術(shù)實(shí)踐和不斷演出的歷練,余祥云高興地看到,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培養(yǎng)過的孩子,都會說一句相同的話“閩劇還是很好聽的”。
余祥云告訴記者,這幾年,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,國家越來越重視挖掘、保護(hù)、傳承傳統(tǒng)文化。閩侯也在加大力度挖掘、保護(hù)以曇石山為代表的傳統(tǒng)文化。文化的大發(fā)展、大繁榮,激發(fā)了全社會投身文化事業(yè)的熱情。
“挖掘、保護(hù)和弘揚(yáng)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傳承。”余祥云和老團(tuán)員們形成了共識。而要傳承,除了教授“大學(xué)生”,打好群眾基礎(chǔ),更要激發(fā)“小學(xué)生”的興趣。如今的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,有一半是青少年。余祥云告訴記者,只要培養(yǎng)出他們的興趣,抓住他們的心理,就成功了一半。通過藝術(shù)實(shí)踐和不斷演出的歷練,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培養(yǎng)過的所有孩子,幾乎都和余祥云說過相似的一句話,“閩劇還是很好聽的。”
正是逐漸認(rèn)同了傳統(tǒng)民樂,孩子們有了更大的勁頭。來自荊溪的徐燕明,今年剛上初一,已經(jīng)參加樂團(tuán)2年了。今年5月,徐燕明將與另外4名團(tuán)員一同參加上海“星星火炬中國青少年藝術(shù)英才(二胡)推選”全國總決賽。另有多名孩子獲得“閩江之春器樂大賽”笛子獨(dú)奏一等獎、“福建省鄭奕奏閩劇金獎大賽”銀獎、“世界十邑閩劇票友大賽”銅獎等。
“跳動在鄉(xiāng)間的民族音樂,是最美的音樂。積極挖掘民間音樂,走通俗與高雅相結(jié)合之路,以滿足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,是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的努力方向。”余祥云說,為了這個(gè)目的,他愿意付出所有努力。
這些演奏者都是閩侯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的成員。團(tuán)員中年齡最大的65歲,最小的不到5歲。目前,樂團(tuán)中經(jīng)常參加活動的有36人,一旦有大型活動,可達(dá)57人。
5年來,他們風(fēng)雨無阻,在千年古邑閩侯,把興趣、愛好與挖掘、保護(hù)、傳承民族音樂結(jié)合在一起,讓民族音樂在鄉(xiāng)間跳動。在第二屆省社區(qū)文化藝術(shù)節(jié)中,他們演奏的余祥云改編的《春韻》,獲得整體節(jié)目第二名、器樂合奏第一名的好成績。
癡迷民樂的余祥云自己學(xué)著做了把京胡。1977年恢復(fù)高考,靠著一手京胡技藝,他考上了福建師范大學(xué)藝術(shù)系。
說到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,先得認(rèn)識一個(gè)人,他叫余祥云,閩侯一中高級教師、省內(nèi)頗有名氣的二胡演奏家。
今年51歲的余老師,是閩侯白沙鎮(zhèn)大目埕村人。祖輩、父輩癡迷閩劇,奶奶曾創(chuàng)辦了村里的閩劇團(tuán)。小學(xué)開始,余祥云就跟隨父親、堂哥學(xué)習(xí)京胡,唱京劇、閩劇。“那時(shí)候,完全出于興趣,他們也沒經(jīng)過正規(guī)訓(xùn)練,主要靠自學(xué)。”
上中學(xué),余祥云擁有了自己的京胡。“打了條老蛇,弄幾塊竹片,就自己學(xué)著做了。”余老師說,當(dāng)時(shí)一把京胡至少要7至8元,相當(dāng)于一個(gè)月的工資,沒有錢,只能自己動手。
高中時(shí)代,余祥云參加了公社組織的文藝宣傳隊(duì),一把京胡讓他感受到了價(jià)值和樂趣。1975年高中畢業(yè)后,余祥云回家務(wù)農(nóng),在那兩年半的日子里,白天勞動,夜晚無論多累,他都要拉上幾段。1977年恢復(fù)高考,余祥云靠著一手京胡技藝,考上了福建師范大學(xué)藝術(shù)系,主攻二胡。
1982年大學(xué)畢業(yè)后,余祥云分配到南平師范。除了教授二胡,他還執(zhí)教鋼琴、音樂理論等,并任音樂教研組長。
2000年,余祥云調(diào)回老家閩侯,任縣一中音樂老師。無論在哪里,處在人生哪個(gè)階段,余祥云始終保持著對民族音樂的癡迷。
2003年,余祥云牽頭成立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。教師、醫(yī)生、機(jī)關(guān)干部、拖拉機(jī)手等各行各業(yè)的人,為著挖掘、保護(hù)和弘揚(yáng)民樂這一共同目標(biāo),走到了一起。
閩侯是閩劇的發(fā)祥地,還曾是十番音樂、評劇、折子戲等民族音樂的沃土。然而,回到故鄉(xiāng)的余祥云卻發(fā)現(xiàn),這里已很少人唱,更少人懂。
嚴(yán)峻的現(xiàn)實(shí),讓余祥云心痛不已。難道就讓民族音樂這樣消亡?作為一個(gè)民族音樂的研究者和愛好者,他覺得應(yīng)該做點(diǎn)什么,讓民樂重新在閩侯“熱鬧”起來。
2003年8月,閩侯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正式成立。8名因?yàn)閻酆米叩揭黄鸬娜耍蕴脱徶昧硕⒁繇憽P(yáng)琴等,在余祥云家20多平方米的雜物間,奏出了美妙的民族之樂。
余祥云對團(tuán)員的音準(zhǔn)、節(jié)奏、手勢、坐勢、工序等逐一進(jìn)行指導(dǎo),并布置“作業(yè)”讓團(tuán)員練習(xí)。團(tuán)員演奏水平很快得到提高。因?yàn)橛辛诉@個(gè)樂團(tuán),有了余祥云的專業(yè)指導(dǎo),這個(gè)團(tuán)吸引力越來越大。愛好民樂的群眾紛紛加入,有教師、醫(yī)生、機(jī)關(guān)干部,也有學(xué)生和拖拉機(jī)手。
今年63歲的吳海光是首批加入樂團(tuán)的成員。他對二胡很感興趣,但是“曲不成調(diào)”。“以前求教無門,只能自己瞎擺弄,水平有限。現(xiàn)在,有了余老師的悉心指導(dǎo),進(jìn)步顯著,我已是業(yè)余六級水平。”
張光巖是閩侯上街的農(nóng)民,平時(shí)靠開拖拉機(jī)運(yùn)貨過活。遇到要白天合練,張光巖定會放下手頭的活,趕到縣城參加,一天幾百元也不賺了。“我們都是‘大學(xué)生’――大了的學(xué)生,以前雖然想學(xué),但沒人教,因此要更加認(rèn)真練習(xí)。”
5年來,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已先后創(chuàng)作、整理、排練了多部鄉(xiāng)土民樂及閩劇、京劇改良曲子。大型民族管弦樂《春韻》、《二泉映月》、《京調(diào)》等已排練成熟。目前,正在緊張排練由傳統(tǒng)閩劇改編的《寶蓮燈》、《曲判記》唱腔片斷和現(xiàn)代京劇《杜鵑山》、《亂云飛》等民樂合奏曲目。“以曇石山為背景的大型民族管弦樂《曇石山隨想》,已創(chuàng)作了兩個(gè)部分,剩余三個(gè)部分正在創(chuàng)作中。”余祥云說,傳統(tǒng)閩劇的缺點(diǎn)是經(jīng)典唱段幾乎沒有,更沒人能唱得清楚。通過改編,如今在排練演出過程中,許多群眾都很驚訝,還有這么好聽的閩劇。
通過藝術(shù)實(shí)踐和不斷演出的歷練,余祥云高興地看到,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培養(yǎng)過的孩子,都會說一句相同的話“閩劇還是很好聽的”。
余祥云告訴記者,這幾年,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,國家越來越重視挖掘、保護(hù)、傳承傳統(tǒng)文化。閩侯也在加大力度挖掘、保護(hù)以曇石山為代表的傳統(tǒng)文化。文化的大發(fā)展、大繁榮,激發(fā)了全社會投身文化事業(yè)的熱情。
“挖掘、保護(hù)和弘揚(yáng)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傳承。”余祥云和老團(tuán)員們形成了共識。而要傳承,除了教授“大學(xué)生”,打好群眾基礎(chǔ),更要激發(fā)“小學(xué)生”的興趣。如今的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,有一半是青少年。余祥云告訴記者,只要培養(yǎng)出他們的興趣,抓住他們的心理,就成功了一半。通過藝術(shù)實(shí)踐和不斷演出的歷練,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培養(yǎng)過的所有孩子,幾乎都和余祥云說過相似的一句話,“閩劇還是很好聽的。”
正是逐漸認(rèn)同了傳統(tǒng)民樂,孩子們有了更大的勁頭。來自荊溪的徐燕明,今年剛上初一,已經(jīng)參加樂團(tuán)2年了。今年5月,徐燕明將與另外4名團(tuán)員一同參加上海“星星火炬中國青少年藝術(shù)英才(二胡)推選”全國總決賽。另有多名孩子獲得“閩江之春器樂大賽”笛子獨(dú)奏一等獎、“福建省鄭奕奏閩劇金獎大賽”銀獎、“世界十邑閩劇票友大賽”銅獎等。
“跳動在鄉(xiāng)間的民族音樂,是最美的音樂。積極挖掘民間音樂,走通俗與高雅相結(jié)合之路,以滿足群眾的文化生活需要,是曇石山民樂團(tuán)的努力方向。”余祥云說,為了這個(gè)目的,他愿意付出所有努力。
更多: